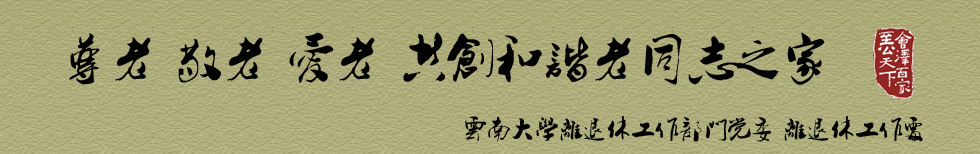一位云大幼儿园时的发小在微信群里说:“张延理还可以写写他爸爸当年邀请关肃霜来云大演戏的盛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因此得以一睹名角的丰采,向云大人普及戏曲知识和表演艺术,这可是他的一大功劳。”看完这段话,确实让我回想起我父亲(张友铭,1912.10-2001.12,北京人,云大中文系副教授,语言教研室主任,云南省语言学会理事、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顾问)所参与过的云大戏曲活动。戏曲之所以能在云大普及,得益于当年的云大有着尊重个性发展的良好人文氛围。老云大的戏曲文化确实不能小觑,它是当年云大校园文化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云大戏曲活动的一些往事写出来,一是表达对云大老辈戏迷们的怀念,二是借回忆文字,让人们去感受云大的那份深厚文化底蕴。也正如赵国平(老云大子女,网名“笛韵如水”,网文《翠湖边长大的孩子》的作者)在微信群中所言:“草民的点滴野史其实就是一部真实的大历史。”但愿我的回忆能为云大留存下那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往昔时光。
以往每当父亲提到京剧时,往往会以感叹惋惜的语气提到昆曲,进而以怀念口吻提到陶光和吴征镒这两位长辈,在我的追问下,得知他们两位都是父亲在昆曲方面的良师益友。父亲说,当年清华、北大、南开都还在昆明时,云大就有了昆曲社,它是由云大中文系的昆曲爱好者们建立的,建立的时间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期。由于昆曲社活动很红火,甚至将联大和社会上的昆曲爱好者都吸引过来了,很快就形成了以两个台柱支撑、众曲迷纷纷尾随学习的局面,其中就有打小就喜爱昆曲的父亲。
那时,云大中文系热爱戏曲并对戏曲文化进行研究的大有人在,突出的就有四位。他们在“戏剧学”的研究上都颇有造诣。刘文典老伯就是云南地方戏滇戏的铁杆“粉丝”,他与被称为云南“滇戏泰斗”的栗成之是至交。1949年,京剧大师马连良到昆明演出,曾与栗成之会面,刘文典先生就亲笔题“北马南栗”四字,制成锦旗赠马连良。他的喜好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戏曲的关注和爱好;徐嘉瑞早年就从事元剧语言研究,先后出版了《金元戏曲方言考》《云南农村戏曲史》《大理文化史稿》等;叶德钧在戏曲文化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编著了《戏曲论丛》《胡笳十八拍考》《宋元明讲唱文学》等,后人为其整理编辑出版了《戏曲小说丛考》;范启新是20世纪30年代云南历史上第一个艺术师范学校表演科毕业的学生,是云南近代话剧发展的见证人,曾与曹禺同台作艺术讲座。20世纪50年代,云大中文系的师生曾在大课堂进行过多台话剧表演,如:《十五贯》、《阿Q正传》等(我父亲就饰演了话剧《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这些话剧的导演都是范伯伯。四位老伯对戏曲的热爱和研究对云大中文系戏曲文化氛围的形成起到了奠基、引导的作用,这也就使昆曲社在云大建立势在必然。

图为父母、二哥和我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父亲写下了“一九五四年元月四日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次日”。
我自小就常在家里听父亲哼唱昆曲,其声调悦耳,韵声悠长。有时看到父亲手里拿着线装书,不是读而是在唱,其韵调与我听他哼的昆曲相同,仔细一看,父亲是在将书上的诗或词用昆曲的调唱出来。以前我仅知道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后来才得知它发源于14世纪元代的苏州太仓南码头,被誉为“百戏之祖”,是中国的古典歌剧。它以鼓、板控制演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唱腔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边唱边舞,追求完美的舞台置景和艳丽的服饰。最核心的是它蕴含了音韵学、训诂学、注释学、古典文学、古典诗学、古典词学、古典音乐学、古典舞蹈学、戏剧学、历史学、表演学、美术等知识,向人们展示着世间的万般风情。昆曲中的许多剧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了解了昆曲的相关知识后,我感慨当年云大的国学文化底蕴之深厚!虽然当年云大昆曲社的规模并不大,但没有适合昆曲成长的土壤,如此高雅的戏曲艺术就根本不可能植根,更别说成长壮大。当年云大的国学水平不处于历史巅峰,何时才为历史巅峰?我更感慨的是,两位台柱陶光和吴征镒对云大昆曲社的贡献。
陶光是满族,他的祖父是宣统三年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被起义新军所杀的托忒克·端方。由于辛亥革命后满族受到打压和歧视,再加上他祖父如此出名,他不敢用托忒克·光华的满族姓名,取了其祖父名号陶斋中的陶和其名字中的光合并为其姓名,而将他托忒克·光华的满族姓名抛弃,不向任何人提及家事。出生于官宦人家的他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因嗜好昆曲,拜号称南徐(徐凌云)北溥(溥侗)之一、北曲泰斗爱新觉罗·溥侗为师。溥侗为清代皇族,别号“红豆馆主“,与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溥侗精于昆曲、京剧,通晓词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规定情境有深刻领悟,又兼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自1930年起,就在清华大学讲授昆曲。身为清华中文系学生的陶光就此更进一步得其亲传,昆曲技艺水平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图为昆曲照片。
云大昆曲社的策划者就是陶光,当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老师,选云大建立昆曲社团,表明云大的文化氛围确实吸引人。昆曲社建立后就一直在晚翠园内活动,陶光唱的是小生,嗓子好,声音宽、圆、亮、足、有力度。是同样喜好唱小生的曲友(譬如我父亲)难得的最好的效仿对象。
大家所熟知的吴征镒是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扬州著名的文史世家,他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很早就学会了唱昆曲,特别擅长唱老生。由于身体好,中气足,能将很长的曲段一口气唱下来,这能耐连一些专业演员也做不到。当年正在西南联大教授植物学、同时也被聘为云大兼职教师的他也加入了云大昆曲社,这样他和陶光同时成了云大昆曲社的台柱。
之所以称他们为台柱,是因为他俩昆曲的唱、念技艺在社内是最高的。陶光所唱词位较密、拖腔少、曲调高亢激扬、慷慨朴实,多用于表达激情迸发的北曲;吴征镒所唱词位疏松、拖腔多、旋律流利、曲调柔情似水,多用于表达内心深切细微情感的南曲。正好是曲友们学习、模仿昆曲不同特色的最佳机会和场合,这确实是曲友们的福分!父亲之所以怀念当年的昆曲社,原因也正在于此。遗憾的是他们两位先后分别离开了云南,陶光虽然在清华光复后投奔恩师刘文典来到了云大中文系任教,但却于1948年受聘到台湾任教;而吴征镒也于同年离昆前往北京清华深造,从此云大的昆曲社活动就渐趋衰弱,直至停止。
一九四九年后,云大建立了工会,丰富教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也就成了工会一项工作内容。在选择既有一定基础,又能吸引教职员工广泛参与的戏曲娱乐项目上没选昆曲而选定了京剧,我猜测原因在于昆曲太小众,京剧更普及,没上过学的小孩和老太太也能听懂、看明白。当时的云大京剧迷较多,并具备能扮演生、旦、净、末、丑各角色(行当)的人才,工会开展职工娱乐活动就是要大众参与,这样在校工会领导下的一个京剧爱好者群体就诞生了。没有什么组织章程、领导人之类的,只有具体的召集人,此义务就由我父亲担当了。
最初,就如同现今一群老戏迷相约定期定时到某公园内某固定地点边拉边唱过戏瘾一样,父亲他们一拨戏迷每周末晚上都汇集到工会俱乐部举行清唱聚会,当把所选定剧目的某一唱段告知担当琴师的父辈后,京胡、二胡一响,吟唱开始,唱者沉醉于自娱自乐之中,听者也在欣赏中得到身心放松。但如此每周一次的清唱并不能满足戏迷们的需求,要当票友(会唱戏、或会伴奏,并不以演戏为谋生专业的爱好者)才过瘾,要到大课堂的舞台上去表演。这实际上是每个戏曲爱好者技艺发展的必然。校工会不但鼓励而且支持,添置了锣鼓等乐器,然种类繁多、价格昂贵的行头(指戏装、头饰、戏具、道具等)就只能租或者借了。当年,云南省只有一个专业京剧团体——云南省劳动人民京剧团,要租或者借行头只有去团里。而这租或者借的任务就落到父亲头上了。

图为《铁弓缘》中关肃霜饰演的花旦角色。
省劳动人民京剧团于1950年成立,地址就在民生街与五一路交界处北端的云南大剧院里。团长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奎官,他擅长饰演花脸(戏中脸画彩图的角色,譬如:张飞)、武生(戏中武功见长的男性角色,譬如:武松),尤其是他在经其创新改编的《通天犀》中所饰演的青面虎,在国内堪称一绝,戏中他在罗圈椅上的表演技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他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与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赵如泉、林树森、赵君玉、白玉昆并称中国京剧界的“八骏马”,驰誉国内外。
要租借行头就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当每次确定要演出的剧目并拟出所需行头清单后,父亲就前往剧团向刘奎官商借,其中有一次还带我前往,记得是到他居住的家里,那是位于五一路上正对民生街口的一座“一颗印”老民居院落的正房楼上,老人虽然身体偏瘦,但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尊父亲之命称呼他“刘爷爷”后,老人笑呵呵的,特别慈祥。看得出来刘爷爷对读书人特别敬重、特别客气,他不但答应无偿将行头借给云大,而且还仔细审核清单所列项目和数目是否齐全。
多次借物来往之后,父亲与他相处也很融洽了。戏迷都很想欣赏到他的演出,于是,经提议且工会同意后,父亲很谨慎试探性地提出希望他能到云大给广大师生进行表演的恳求,没想到刘爷爷很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刘爷爷的舞台形象就出现在学校大课堂的舞台上了。他把他最好的剧目—《通天犀》展示出来,虽然那晚他只演了其中的几段,但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酒楼”、“罗圈椅”、“朝天蹬”。与每次看大课堂的京剧表演一样,我都没有票,这不但是因为云大师生对能看到京剧名角的表演非常期待,踊跃前来观看,大礼堂里总被坐满,也是因父亲从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我只能提前抢占大课堂外侧最靠近舞台的窗台,蹲在上面观看。我真感慨他仰面后翻弯下去叼酒杯的身段柔软;佩服他飞快地在罗圈椅上做出飞、旋、跨、立、卧等动作,真是身轻如燕、运作自如;惊讶他朝天蹬时的纹丝不动,要知道他是我亲眼所见,完全配叫爷爷的人了,这一切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完全忘了蹲窗台的危险和疲累,我相信当年看过他这场表演的人一定会与我同感。
解决了行头问题,父辈们的票友梦可以实现了,只要主要角色齐全,能赶上学校举办晚会,父亲他们都要争取上舞台表演一回,从简易的折子戏(只演一个剧目中一段)到全本(将整个剧目从头到尾完整表演),只要能唱得下来,都挨个地演。但排练是必须的,因为他们终究是业余爱好者啊!为了解决缺跑龙套(指剧中扮演侍从或兵卒的角色,负责在剧中助威呐喊或烘托气势,以表示人马众多)的问题,父亲他们就到女同志居多的图书馆和卫生科去动员,果然有不少阿姨报名愿跑龙套,连我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参加了几次表演,使得观看自己母亲在台上一举一动也成了我看戏的内容之一了。当然,看父亲的表演是最主要的。现在能回想起戏名的折子戏有苏三起解、二进宫、借东风、三娘教子、三堂会审、三岔口、武家坡……能全本戏都演下来的就少了。但父辈们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多练唱段、多背台词,终究还是演出了一些全本戏,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打严嵩、玉堂春、打金枝、甘露寺……

图为中文系《阿Q正传》全体演职员合影。
在一次同学群内聊天谈到我父亲唱京剧时,胡洁接帖言道听他父亲(胡以人,时为云大农学院教师)说,一次在她父亲为我父亲的表演拉京胡演奏过程中,突然父亲所戴文生巾(小生角色戴的帽子)脱落下来,按演唱过程中琴声必须跟随好演唱节奏这一京剧伴奏的规矩,胡洁的父亲本能的紧盯父亲的嘴巴,只要父亲一停唱,琴声立刻也得断,但却见父亲不顾台下一片哄笑声,很镇定的边唱边将帽子扶正,继续表演下去。这也成了云大戏迷中的一件轶事趣闻。当然喽,至于走错台步方向、对错词、唱走调等不该出现的错误,在这拨戏迷的表演中是难免的了。
数年前,为母亲的事到学校离退办,在周健民老师办公室聊了起来,周健民谈到离退办老师到全国各地走访异地离退休同志过程中,一位中文系的学生询问当年教他的老师们近况,谈到我父亲时,说有一件事他印象很深刻:若讲课内容与京剧的某个剧目内容相关,就见父亲放下书本,停止讲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清唱起京剧来。唱毕,没忘了将唱段内容与讲课内容串通起来进行讲解。听罢周健民老师的转述,不由惊讶父亲着迷京剧到如此程度。这可能也是当年云大老戏迷们的一个缩影吧!更是老云大教学风气使然。

图为刘文典(左一)与刘奎官及其孙女合影。

图为刘奎官饰演关公剧照。
云南京剧演员中,除了刘奎官,就数关肃霜在云南乃至全国有名气了。关肃霜原名关鹔鹴,由于鹔鹴笔划太多,周总理建议她改成肃霜。鹔鹴是传说中的五方神鸟之一。周总理曾风趣地对关肃霜说:“把旁边的鸟字拿掉,你就落在了地上。全国这么大的地方任你走嘛”。关肃霜生前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剧协主席、省京剧院院长。
因常去借行头,更何况父亲本身就是一个超级戏迷,没多久父亲与剧团里的不少演员就相知相熟了。父亲要找剧团里的演员,就选被找者有演出的晚上去,还挑被找者正在后台休息的时段,我随父亲去过几次。至今印象极深的一次是父亲去找关肃霜,在舞台后面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关肃霜,当时她已经画好妆,正候着台,父亲要我称呼她“关阿姨”,她慈爱的摸了摸我的脑袋应答了我,随后就是父亲与她交谈了,而我则好奇地在楼上四处观望。不一会儿,剧务上楼通知关阿姨该上场了,父亲也就起身叫上我准备告辞,此时就见关阿姨走到桌前拿起一个碗仰头将碗内食物一口气吞下,转身下楼去了,我特别好奇地悄悄问父亲,父亲回答说,碗里是生鸡蛋,吞下它能润喉,防止唱着唱着出现喉咙嘶哑。事后我更得知,当年临上场前吞生鸡蛋是流传在戏剧演员中的一种习惯。有了邀请刘奎官的先例,邀请关肃霜到校演出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与刘奎官一样,关阿姨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从我与他们的接触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京剧演员们都把高等学府视为神圣高雅的殿堂,把读书人都尊为斯文学者,表情中流露的是尊敬和羡慕。我想她之所以接受父亲邀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京剧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接受京剧、热爱京剧。
在我的印象中,关肃霜先后两次受邀到云大给广大师生表演。头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一次是在60年代中期临近文革前。第一次演唱的是全本《铁弓缘》,这是最能代表关肃霜京剧艺术水平的一出戏,剧团很重视这次演出,派出了最强阵容,全是省劳动人民京剧团一线主要演员:关肃霜、高一帆、梁次珊、贾连城、关肃娟等。戏中关肃霜饰演的角色在跟随母亲(关肃娟饰)卖茶水度日时以花旦出现,当杀死恶霸不得不男扮女装外逃时是个文小生,而最后闯关杀仇人救未婚夫时是威武的武小生,一出戏关肃霜实际就扮演了三种角色,也只有她这样全能的人才才能做到。看这出戏要欣赏的也就是看她在演不同角色时的精彩表演。
关肃霜到云大表演的第二个剧目是现代京剧《黛诺》。这是由1963年出版的云南民族题材电影文学剧本《景颇姑娘》改编而成,反映的是景颇族人民反对反动山官统治,迎接解放军,开创新生活的历史进程。以剧中女主人翁的名字黛诺作为剧名。为演好这出戏,关肃霜等人曾经到德宏州潞西县三台山和瑞丽县勐休乡南京里等景颇族聚居地区进行生活体验,吸取实际生活素材。该剧于1964年赴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就受到戏剧界的重视和好评。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特意把关肃霜等主要演职员请到家中做客,并对他们说:“你们演了很多(民族)戏,作了很大的努力,我很高兴。”
云大的戏曲热最活跃的时期应当是在“反右”之前,记得在九家村四号父亲的住房兼书房里传出他唱戏声音最多的时期也是那段时间。“反右”一来,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别说我爬大课堂窗户看父辈唱京剧不可能了,父亲他们的清唱聚会也难以维系了。戏瘾犯了怎么解决呢?父亲就一靠自娱自乐,在家里哼唱;二买唱机(留声机)和京剧唱片,一个人听或约着戏迷一起听,记得最常来家里听的是李云鏊;三是上剧院看演出,父亲在省中医院刚动完手术还未出院,听说梅兰芳的《洛神》拍成电影在昆明放映了,立刻要我去买票,随后由我搀扶着走到人民电影院痛痛快快的过了一场戏瘾。
文革开始后,云大开展的戏曲活动彻底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革命京剧,任何一个小孩打小学起听得最多、唱得最熟的也都是语录歌和现代京剧了。
云南大学原中文系已故副教授张友铭之子 张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