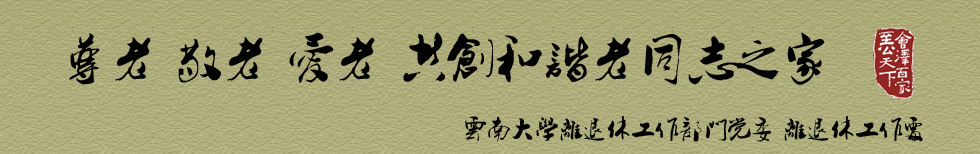引言
每年,云南大学的银杏道上铺满落叶之时,新生入学了。这些刚入学的学子都怀着不同的人生梦想进入高等学府。针对这些准大学生进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崇高理想教育理所当然。但是,笔者认为,对他们进行校史的教育也是当务之急。
教育的发达,在于体现人的素质,人的素质高低,并非完全是从课堂上得到的文化知识,关键是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接受的引导。西方启蒙,功在大师,日本启蒙,功在教育。大师学者成就之大,在于教育之赐;学子成才之道,也在教育之赐。一所大学的历史不仅渗透学校的发展纪录,而且是这所学校的名片,透视着这所学校的荣誉。所以,对入学新生启蒙教育的第一课应该是校史的教育。
在会泽院“大堂”,嵌在正面墙壁上方的那两块沧桑的方形石碑《创建东陆大学碑记》、《会泽唐公创办东陆大学记》给人以沧桑的情感,岂是杜甫诗:“结叹随过隙,怀旧益沾襟”的怀旧情结?那是拂拭不去的前尘往事—这就是校史的“启蒙”教育的最好教材。
碑记概说
《创建东陆大学碑记》是东陆大学第一任校长董泽(1888—1972年)撰文,云南名士、国民党元老周钟岳先生(1876—1955年)书,此碑立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会泽唐公创办东陆大学记》则是在唐继尧(1884—1927年)逝世那年(时年43岁),即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23日病逝,是年9月“东陆大学同人公立”,以示纪念创办人唐继尧,碑曰:唐公以在滇创办大学“引为己任”,其为东陆大学之操心是他“精神求久之表现”,故不能忘记,“因书其崖,略以告来叶(注,即后代之意)”。此碑是昆明德高望重的著名教育家、书法家陈荣昌先生(1860—1935年)所书。先生于清末担任昆明经正书院山长(院长)和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教务长)等职;他时任翰林院编修时,首荐梁启超、袁嘉谷;他精于书法,擅长诗文,有"滇南一大手笔"之誉。昆明当年的护国门碑作誉之“巨笔敢拄千秋义”。其著作颇丰。当年昆明商业繁华之正义路等街道的大商号的招牌均为陈荣昌先生所书。他所书商号和对求书者收取的润笔费多作为捐款,救济他人。他为官清廉,晚年贫困而卒。俗话说:“善财难舍。”如陈荣昌先生的善举,可圈可点。其善行今日也大有文可作;其故事今日亦大有书可抒!卓尔大贤,频添人间一段传奇。
这两块石碑记录了时任云南都督唐继尧创建云南大学的思想基础和挫折、过程,以及学校的规模和编制、人员等变化情况和办学思想等。
碑文记叙,云南“处边陬开化较晚,外则强邻福处,内则地利未辟,加以交通梗阻,学子艰于升进,识者咸以筹建大学为治滇尧囿。”基于当时之滇情,唐继尧于民国九年(1920年)“毅然废督裁兵,振兴文治,作救国之远图”,遂与留美、留日归来的云南有识之士董泽和王九龄(1880—1951年)酝酿“建议立大学”,因“帑绌不胜”(经费不足),唐继尧即提出“捐资助学”之议。碑文记“无何,因故中缀”,指(指民国十年至十一年间,即1921至1922年间)因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1883—1922年)不满唐继尧出兵川滇,联衔滇军将领迫唐继尧通电辞职,寓居香港。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唐继尧重掌云南政权,历史称之唐继尧“二次回滇”。周钟岳先生在《会泽唐公墓表》中道:“公自再任滇政,以国内兵事频仍,徒耗实力,遂通电宣布废督裁兵,一志整顿内政。”如此,又以董泽为主,把筹备大学之事提到议事日程,“校宇”选昆明城北之东西走向的商山山脊之上的原明清贡院为校址,所谓“左金马,右碧鸡,枕蛇山,面翠湖,所诣他省所无”;其主体标志性建筑——95台阶之上的会泽院,由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云南昭通籍学子张邦翰先生(1887—1958)所设计,民国十二年(1923年)奠基,一年后建成。东陆大学经一年的筹备,得到云南社会各界的资助,公推创办人唐继尧为董事长、董泽任为第一任校长(1922年至1930年),他任职期间,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他说:“要办好大学,物色师资,最是第一要务。”在教学方面强调“本校之教育中心,以实用为依归,故所授课程,务以实际,不尚玄谈。”故当年东陆大学,诸子百家,精勤求道,广事搜罗,态度矜慎,详加厘定,谠员宏论,不胜枚举;敦品励行,苦心劳形,媲美千秋,以为风世的楷模。他提出的办学理念,对云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陆大学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20日“举行开学及奠基典礼,规模渐备”,在学生中倡导“致知力行”,教师则以“自由研究为教旨”,并“奖掖勤修,嘉惠苦学”鼓励努力学习,“凡所以为学子谋者,无微弗至。”当年,唐继尧、董泽提倡这种彰显个性,释放个性,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诚难可贵。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五年间,东陆大学相继完善系科,并聘任清末经济特科的经济状元、滇省名士袁嘉谷(1871—1937年)等,以及留学归来者和外籍名人30余人为师,堪称翘楚。其中尤以袁嘉谷任教时间较长,滇南名士陈古逸先生(1866—1941年)道:教授10年“门墙之盛,一时无两”。他最后一缕尘缘是“要以教育为最!”正可谓:“孜孜不稍倦”也!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三日,创办人唐继尧逝世,重组董事会;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二十四日,“公推龙云为之长”,“基础于是弥固”。
《创建东陆大学碑记》是在东陆大学建校8年,“披荆斩棘,历经艰苦”后立的碑。建校8年来,“巍然日见进展”,其根本“则在事诸人之殚精瘁力,为国家兴文化,地方培人才之所致也。”碑记的目的是“用泐贞珉,以稔当世。使知缔造之不易,而相与维持不蔽焉,则国家地方之幸,抑亦同人之愿也。”
笔者认为,凡是入学的新生必须熟读这块碑记,以颂学校之名,以达追求学校培养人才之利。“计名当计天下名,计利当计万世利”。这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豪言;这是关于名利观的最高境界。
罗马诗人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巍巍会泽楼,纪录创办云南大学的这两块石碑略显沉郁,且不醒目,很少有几个学子去关注。君不见,相邻的昆明第30中学(原南菁中学)那块记录该校校史的碑记是那么气派、那么引人注目。
如何重新“树碑”,方显云南大学之名,笔者认为此乃学府之荣、师生之耀也!正是:“草净堪居鹤;荷香欲醉鱼。”
关于续编云南大学校史的浅见
会泽院的这两块石碑至今分别相距84年,仅纪录了创始人对云南文化贡献的精神和云南大学前身东陆大学8年来的历史沿革。
当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高校是学术研究的基地,学术水平是高等学府的基本定位。在《创建东陆大学碑记》中,记载了袁嘉谷等30余位中外名士受聘东陆大学。惜乎,未记载他们对学校学科建设、发展的贡献,以及学术建树。岁岁年年人不同,明月不沉,哲人不朽,作为校史,对这所学校大师的学术贡献、人文传统、治学风格及办学特点的记述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这所学府知名度的标志。所以,我们在续云南大学校史的时候,系统记载从东陆大学到云南大学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是云南大学的学术色彩;也是云南大学的精髓。切莫把校史撰写成和中国近现代史沿革似曾相识的版本。笔者认为,云南大学是否可以考虑校史进入科研项目的行列,甚至开设关于我国和英美高等教育的比较学,以及我国著名高校的校史比较学和本校校史的课程,其目的为追述和总结本校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作出贡献。
看不完红尘翻滚,看不尽人海沉浮,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如汉朝司马迁曰:“述往事,思来者。”只有校史才能记录学府传播文化不灭的辉煌。
毛祥麟